冰锋!2021年中国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间撷取时代精神( 四 )

文章插图
不过,笔者在这里不愿深究认识论上的真假与作者和读者为何都对非虚构兴趣盎然,而是仅仅想要指出:如果非虚构能够提供给读者一段蕴藉时间、富有意义的故事,那么它们毫无疑问与虚构作品同属于叙事文学,而这两者均判然有别于默认取消叙事的新闻、短视频、街头巷脚的见闻乃至为科学逻辑话语主宰的论著。举例来说,《黑梦》是宁肯系列小说《城与年》的压轴之作,在系列小说以外,他还有一部以“城与年”为题的散文集。我首先读到的是作为散文的《城与年》,等到他以此题创作小说,原先那些长短不一、追忆性质的片断,也就被重塑为一段完整而连贯的叙事。就阅读感受来说,小说《城与年》的质地要远远丰厚于散文。
袁凌对当下非虚构“隐喻”指向的不满,同样令我印象深刻:“写庞麦郎的人是真的关心他的生活困难吗?不是的。其实庞麦郎隐喻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在他看来,意义应当自行呈现。不过,如若以这个标准来重新划界,诸多调查性质的非虚构恐怕也就无从谈起。这里我主要想谈一下杨潇的《重走》与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

文章插图
在谈到《重走》的缘起时,杨潇认为有两点原因促成了这部非虚构的诞生:首先,在1938年2月至4月之间,长沙临时大学是如何南迁至昆明的?关于这段“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一千六百公里,从长沙经湖南、贵州,最终抵达昆明的历史,殊少有读者关注。其次,一个反思性质的原因也推动着他重新踏上八十多年前那些青年的道路:辞掉工作一年后,他遭遇了“存在主义危机”。如果“湘黔滇旅行团”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本国与反躬本心之举,那么杨潇则不仅渴望用行动重建自我,还希冀在1938年的历史中打捞出得以解释当下的答案:“譬如,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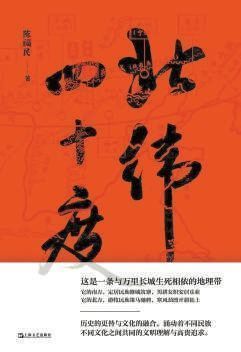
文章插图
《北纬四十度》与《重走》相近,一样是以现实的行走呼应历史,也一样是在历史中寻求一种指向现实的教益。陈福民先生是在历史概念与地理概念的北纬四十度中,看到了一个文化概念的“北纬四十度”。毫无疑问,它首先意味着民族冲突——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定居民族两千余年的缠斗里诞生了无数悲歌;但也意味着民族融合,因为冲突导致互相学习——如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推行的“胡服骑射”,并进而“把自己变成对方”,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将国都由大同南迁至洛阳,推行易服、变语、改姓等改革。在冲突陷入僵局的时候,从中又诞生了“和亲”。在作者眼中,正是这条一以贯之的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主线,锚定了北纬四十度这个漫长故事的走向,而这个故事的内核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汉族、匈奴、突厥、鲜卑、契丹、满蒙渐次褪去了过于耀眼的民族身份,它们消融于混合多元的文明体系里共持的一种认同。
【 冰锋!2021年中国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间撷取时代精神】附提一句,我对袁凌的非虚构写作充满敬意,但我同样喜爱以上这些具有象征、隐喻色彩抑或带有强烈反身冲动的作品。以我浅见,仅就迅疾地捕捉时代精神与回应现实的能力,这类写作并不逊色于虚构作品。
徐兆正,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
- 童书书单
- 中国经济#2021年度经济学图书有三个特点:思想性、历史叙事及学科交叉
- 好书&《2021年成都儿童文学年度综述》发布,来看看去年有哪些好书?
- 年度|《2021年成都儿童文学年度综述》发布,来看看去年有哪些好书?
- |2021年10部惊艳了时光的都市剧,寒假剧荒的小伙伴们快看过来
- 古言小说#2021年5本虐心古言小说,催人泪下,虐的肝疼,高质量好文
- 中国文学@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14幅书法真迹鉴赏,网友:不愧是民国才子
- 长篇小说!2021年“成都小说”推出了哪些重磅作品?这份年报给了我们答案
- 发表了|2021年“成都小说”推出了哪些重磅作品?这份年报给了我们答案
- 中国文学&他比李白更狂,鲜有人知道,一生落魄留下几多千古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