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帮助莫言获诺贝尔奖的翻译说《红楼梦》根本入不了诺奖的门!( 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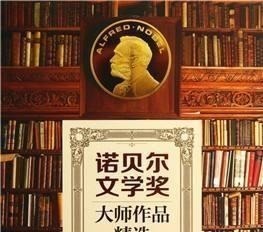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所以,音乐,我们叫弦外之音。画,则曰画外之境、境外之象。文,则曰言外之意。无论诗、书、画,要笔不到而意到,笔不尽而意周,笔尽而意不尽,才能有味道、有境界、有诗意。“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所以,我们爱喝茶,不爱喝白开水。我们也不喜欢喝只煮一遍的咖啡,而是一泡、二泡、三泡,四泡、五泡、六泡,七泡、八泡慢慢地倒噜来倒噜去意犹未尽的茶道。不光茶的味道,还有水的味道(一如书画等艺术“知白守黑”)。中国的艺术,其玄妙之处,就在这样一个含蓄的说而不说不说而说意犹未尽的味道之中。西方人选美,有明确的三围指标,精确到毫米。我们东方呢?“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宋玉两千年以前就说了。如直白而不含蓄,则艺术性降低,乃至于不是艺术的。苏轼那样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宋之冠,诗、文那么好,还被后人评为太直白太直露。对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西方人,要完全读出这种含而不露的味道,几乎是很难的。而要进入到中国艺术的情态意态以至汉字象形意象思维当中(尤繁体字),更不可能。就是说,葛浩文及西方读者,无法一如中国人那样来欣赏中国艺术,他们很难和中国的文人一样进入一种诗意的情境意境当中。一部《红楼梦》,之所以让数百上千万的中国读者着迷,让历代红学家们钻之弥深而不能自拔,难道仅仅因为钗、黛她们这些贵族小姐与公子哥的爱情故事与生活?当然不是。它的内容太丰富太复杂,我们姑且不论。简单比附,《红楼梦》其实就是一首诗,一首古代文人玩的诗。诗比女儿,女儿比诗。曹雪芹把世间之最美,给了这些女儿,给了一个个诗一般美的女儿。我们从中读到了曹雪芹的那颗水一样的女儿心!它纯美、隽永、含蓄、幽远、沉厚。曹雪芹悲天怜人,欲哭无泪,以至泪尽而逝。“智极成圣,情极成佛。”曹雪芹大爱无疆,曹雪芹大悲无疆!这些,西方人岂能读得出来?而仅仅把《红楼梦》看作中国贵族生活的记录,那就太简单化了。又譬如,小说一开头大段的铺陈描写,而没有西方小说那种响亮的句子,在葛浩文看来是无用的多余的。如是,王安忆《长恨歌》几大段落描写上海的里弄,就是多余的了。但,这样的小说如此描写,在我们看来一点都不多余。哪怕是不在开头,在中间描述也是必要的。雨果《巴黎圣母院》写巴黎的建筑艺术,不但不多余,而且成了一大特色,成了经典。从人物性格来说,中国人的个性情怀,几乎是在人情世故中展露出来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要想读懂中国小说,不会那么容易。在这一点上,中西社会从古到今,差别向来很大。是故,无论文化、艺术,历史、民俗、人情、言语、审美,一直到思维方式,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方面,中西方比较研究的著作很多,斯不待言。何况直接反应人的小说?正因如此,要直译中国文学作品是很难的。所以,葛浩文采用了二种翻译派别中的意译一派。到底翻译成什么程度(二次创作有人说比原著好),我们不敢妄加评论。我们只能说,面对中国小说,这或许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

文章插图
对于一肚子墨水和学问的中国文人来说,除了人情世故,还有中国文人独有的品味。就是前面所说的韵味、味道。味道,是品出来的、玩出来的,更是闲出来的。无论琴棋书画、诗酒唱和,都是古代文人的一种常态,它们无不是在玩乐中慢慢产生的。而且,是文人的自娱自乐,不是为了让人知道,更不是为了销出(勾栏酒肆商业活动也主要是传播除了少数文人专为歌妓写词也为自娱自乐)。所以,当面对《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歌赋、诗酒唱和、人情世故,西方读者会读出什么来呢?他们读出来的正如葛浩文所说的:觉得多余。而我们呢,恰恰从中读出一种不可穷尽的味道。木心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水中没有水草,单调。有了水草,水好看,草也好看。这水,便是活水。由是而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便发生了巨大的偏差。他们只看水,而我们水、水草,都看。还要看水草与水在一起的妙处。我们以为《红楼梦》是伟大的著作,了不起的小说,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而在葛浩文看来,却是啰里啰嗦贵族生活的普通记录而已。而该写的,又不写出来(实则含蓄隐晦)。以此而论,他们去读《金瓶梅》《醒世姻缘》这样的小说,恐怕就更难读出其味了。西方也有人对这些小说评价极高,但也只是个别的汉学专家,不是普通读者。即便从专家角度来看葛浩文,那么他的这些个观点,也太浅近了。当然,他自己反复强调针对要走出去的小说(的确好心好意让我们感激!)。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以及西方读者)对整个中国小说的一般评价(文中他也提到西方读者的这些反映)。葛浩文翻译的几乎都是现代小说。那么,他对汉学到底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太清楚(介绍说他是著名汉学家未知是否只要研究中国的东西无论古典或现代都可以称为汉学家亦未见诸其传统汉学成果许是笔者寡闻)。但,从葛浩文的一些观念上我们只能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并不能像一肚子墨水和学问的中国文人那样,进入一种传统的审美意趣与语境当中,品品味味,咀咀嚼嚼,拿拿捏捏,乐在其中。而一切为当下、一切为用的思想,必然降低传统艺术与审美的魅力。不是二者矛盾,而是因为现代与传统并没有完全接轨。而以有用无用取舍,更是浅见短视。即便为用,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的延续性,中国作家对本民族传统小说与文学的热爱而受其影响,也是必然而然的。我们只能说,影响不是太多了(他批评中国作家受传统章回小说影响),而是还很不够。本质上,葛浩文的观念,其实就是西方现代商品社会观念的一个反映:既然是商品,就必须销出去。不然,也就不成其为商品,当然也就一文不值了。而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家,恰恰不是为了销出去,才创作文学与艺术作品(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它的最高境界,不是销出去,让更多人喜欢,而恰恰相反——曲高和寡。阳春白雪、高山流水,才是中国文人艺术家追求的至高境地。因此,当以现今社会能不能销出去的观念,去评判小说与文学优劣的时候,必然与传统中的至高境界,产生千里之遥。如是,若以这样的要求创作小说,那就不是中国文学与小说的最高境地了。那我们何以降格以求呢?至于是不是为读者而写,作品本身自会说话。好在,诺奖不过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即便在古代有这样一个奖,就中国文人的性格与心思而言,他们也绝不会为了获一个什么奖才去创作。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建立在西方文化与评价标准之上,用它来评判中国的小说与文学,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正如穿着中国旗袍与巴黎现代流行服饰同台表演,要分出胜负冠亚军一样。只能说喜欢哪一款,但要分胜负却很难。何况,这里面还有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政治与国际背景等复杂因素掺杂其中。因为少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味”,那么“诺奖”的标准,相对于在中国自身的标准,不但不是世界文学的最高标准,恰恰相反:它对于中国文学——降格了!当代中国文学获奖,也只能是一种不幸中的幸运(我们也和葛浩文一样喜欢莫言小说而且无一例外地是从《红高粱》这样优秀的作品开始的但这与“诺奖”无关)。所以我们说,不能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文学和小说的最高奖。尤其面对中国文学的时候,它的标准不但不是最高的,相反,它要比中国文学自身的最高标准,低了一层。正如至今西方人不可能完全明白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绘画、中国的古典诗词一样,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读懂《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但我们却能读懂西方小说等伟大的作品——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值得我们庆幸的。同时,他们读不懂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小说,这不是我们的不幸,而是他们的悲哀。一如至今整个西方世界也不能完全弄懂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对此,我们毫不奇怪。
- 散文!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水平如何?莫言:行文不自然,病态的唯美
- 文学作品$获得诺奖后本应被尊重的莫言,为何惹来诸多诟病?他都做了啥
- 中国文学&莫言获诺奖后,名利缠身俗事不断,但内心仍是创作之人
- 大学|双减去资本化之后,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做规划?选职业学校还是大学
- 王朔$莫言视他为偶像,王朔夸其是人精,陈丹青称:与他聊天是种享受
- 恶霸#《金瓶梅》中连“地头蛇”都不敢惹的恶霸
- 出身@杨振宁问莫言:你我出身不同,得诺奖有何感受,他是如何回答的
- 雷柏|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五个方面对照检查材料大汇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 莫言!为什么坏人总是比好人的心理强大?难道坏人不会内疚吗?
- 文体$读书 | 名家新春荐读之徐则臣
